-
首页
-
- 首页
- 新闻
北大国发院举办专车政策研讨会 交通部主动参会倾听学界建言
发布日期:2015-10-19 10:36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15年10月15日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园的致福轩教室里灯火通明,这盏灯火更像是中国网络约车市场的希望之火。网络约车是一个互联网新技术催生的新事物,像滴滴专车、搭车,神州专车等一系列公司和平台兴起,把传统的出租车市场和私家车的使用都带入了一个历史的新阶段。专车、快车、顺风车、拼车等该怎么管理,一直存在争议。这不仅关乎出租车的改革,私家车的使用,新兴约车平台和多个产业的走向,更直接影响到城市化进程中如何下好交通出行的大棋,关乎城市的效率与民众的生活品质。如果放到更高的改革视角下,这还是计划经济(出租车)与市场经济(网约车)的一次交锋。

选择在10月15日举行研讨会,源于一个很重要的政策背景。交通部刚刚在10月10日出台一个面向全国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向社会征集意见,时间截止到11月9日,只有一个月。如果这个规定得以通过,后果将会如何?规定有哪些地方最需要调整?
紧扣这一关乎诸多利益的时政热点,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薛兆丰教授特别组织各路经济学家、法学家、交通专家及官员齐聚一堂。出席会议并参与讨论的嘉宾除了北大国发院张维迎教授、周其仁教授,还有很多外部嘉宾,分别是国务院研究室工业交通贸易司司长唐元,国家发改委城市中心综合交通研究院院长张国华,全国律协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委员汪涌,工业与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副总工程师何霞,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顾大松,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余晖,中国政治大学副教授王军,价值中国会联席会长张晓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研究员吴一兴,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广州市客运交通管理处处长苏奎,上海三亦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高级研究员徐康明等。
这个研讨会在前期并未对外公开,也并未邀请交通部主政官员,但《暂行办法》制定部门的两位当家人: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司长刘小明,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出租车管理处处长王秀春捕捉到研讨会的信息之后,也主动前来听会并积极参与研讨。
整场研讨会由薛兆丰教授主持,在安排每人约五分钟的发言之前,他本人先登台对《暂行规定》提出自己的解读。他单刀直入,直陈要害,指出这一办法简直就是为专车量身订作的六大杀手锏。分别是第一,多地区报批。我国县一级的单位大概有2000多个,每一个地方都要去申请。第二,强制转变车辆使用性质登记,这点是致命的,是所有杀手锏中最根本的一点。如果强制执行规定,想要开专车一定要注册为出租客运,八年就要报废。第三,沿用数量管制,第四,沿用价格管制,第五,强加劳动关系,第六,强调不得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这些都与市场经济的内涵严重冲突,必须批评。他现场还呼吁大家多提意见,尽最大努力避免出现一部“恶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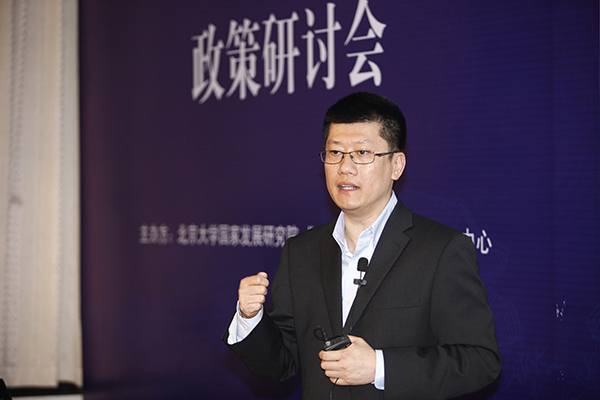
薛兆丰教授工业与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副总工程师何霞结合电信改革的经验做了分析,她提出,作为中央部门,政策监管通常都是两个目标,一是保护消费者权益,二是促进产业发展。同时还要考虑执法的成本问题。网约车的出现不仅使出租车与黑车的二元市场变成了三元,而且迅速崛起,说明符合市场需求。监管可以,但谨记政策的目标,而不是政府的权力。
价值中国会联席会长张晓峰从互联网+的角度对这一政策进行分析,他认为互联网+所带来的最大改变是关系的重塑。决策考虑的第一主体不再是政府、平台,也不是车主,而是消费者。政策应该保护消费者的选择权,同时也要呵护新业态,尤其是明显符合消费者利益的新业态。如果不是工信部放微信一马,如果不是商务部对阿里巴巴高抬贵手,今天的市场又是另一番景象。
广州市客运交通管理处处长苏奎作为政府官员,认为事情已经很急,不能再让子弹飞。如果不对专车立规矩,制度化,出现问题就只能动用司法,而司法成本很高。尤其是中国与英国等相比,法规体系不完善。从实践上来看,专车并非全新的事物,Uber在2009年就已经成立,这一市场要暴露的问题也已经充分。如果出台,这将是全球第一个管理专车的国家级法规。

广州市客运交通管理处处长苏奎国家发改委城市中心综合交通研究院院长张国华认为,互联网+加在哪个产业,哪个产业就会出现“混乱”,但要看看究竟乱了什么,乱的只是老产业的方寸,因为它打破了原有的竞争格局。微信对电信,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银行都是如此。创新会带来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正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属性。如果都高度确定,那是计划经济的典型特征。网约车作为新生事物,明显促进了分工,也通过互联网很好地解决了信用体系问题,不能轻易通过一个法规造成对新生业态的扼杀。
国务院研究室工业交通贸易司司长唐元分享了他刚刚完成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有三个重要发现,第一是网约车改善了出行效率,缓解了出行难。第二是网约车盘活了存量资源,有利于抵制私家车购买,提高私家车使用效率,有利于节能减排。第三是网约车有利于倒逼传统出租行业升级。政府应该利用这个契机,完成对出租行业的改革,而改革的核心就是取消特许经营。

国务院研究室工业交通贸易司司长唐元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指出,交通部面对互联网+所带来的冲击,应该以五个谦逊来对待监管。第一,法律对于新生事物的解释要保持谦逊;第二,权力对于利益要谦逊,不要动用权力与民争利;第三权力自身要谦逊,不要为追求部门权力的存在感而立法;第四,法律技术对具体问题要谦逊,要给新生事物一个避风港,不能抓住一件事打倒一批人;第五,对技术的进步要谦逊。索尼当年录像机推出后,曾经受到好莱坞和电视台攻击。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军认为,中央不要急着出法律。法有好法,也有恶法。好的法律解决问题,恶的法律制造问题。不合时宜的法律一旦生效,一方面把正当活动变成了非法,执法也很困难。另一方面,不好的法律不可能受到尊重,影响法律的威严。专车本质是上共享经济的一部分,而共享经济是人类发展的成果,更集约地使用地球资源。政府对创新的支持不仅体现在为催生创新而进行政策补贴,更体现在对已有创新在立法上的包容性。
上海三亦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高级研究员徐康明认为,在专车管理上要着眼于三个问题。第一,国际做法与法理:国际上有的对网约车支持,有的完全禁止,借鉴国际的前提是考虑本国实际情况。中国对出租车的使用率极高,事关人人出行,一旦政策不当,试错代价极大;第二,政策着眼点:消费者权益,包括乘客的出行权,安全,还有出租车的利益,新兴资本和平台的权益;第三,立场。政府要争取共赢,不能帮助新兴资本灭了出租车,也不能帮助出租车灭了专车,共赢是最好的选择。
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顾大松刚刚参加完交通部的听证会,他主张规定的出台一定要有联动的思维,注意出租车与专车的联动,新利益与旧利益的联动,国营与民营的联动,还有中央与地方的联动。作为政府,尤其是中央,出政策必须有高度,下一盘大棋,而不能简单地站在出租车或专车的某一方。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研究员吴一兴表示,对于网上讨论的几个所谓管理难点或争议点不太认同。首先,专车不是网络出租车,而是全新的模式;其次,专车也不是出租车的补充;最后,专车不是质优价高的代名词。因为认知的误区,暂行规定中有几条明显不合理,比如对市场份额的规定,对跨区经营的管制等都和反垄断法的精神发生冲突,造成法与法不合。
全国律协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委员汪涌是著名律师,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他表示,法律界有一句名言,叫良法善治。不是有法律就有好的制度,法有好法,有恶法。国法不分人情,不能因为出租车好像现在吃亏了就出个法让专车难受。对于暂行规定他建议政府尊重新创新主体,尊重市场,尤其是不能伤害消费者权宜。法律的社会价值在于保护和促进人类的福祉,而不是权力部门划分势力范围的工具。政府提倡简政放权,要想真正做到,唯一的办法就是减人,因为只有还有人在,他就想管事儿,就需要存在感。

全国律协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委员汪涌律师特别闻讯赶来的两位主政者,负责《暂行规定》起草的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出租车管理处处长王秀春,及其上级领导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司长刘小明也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王秀春表示,今天来听会本来是听取专家意见的,没想到意见都如此尖锐,自己如同站到了审判台上。她表示,网约车确实是一个新的业态,交通部也是出于联动管理的思路,同时推出了出租车改革与网约车管理两个规定,而网约车的管理办法相比出租车改革文件更像是副刊、附件。
刘小明表示,研讨会充分体现了北大的民主与科学精神,文件虽然出自交通部,但监管离不开工商与公安等多部门的配合。出租车管理是世界性难题,专车又是世界性新问题,这其中有传统旧势力,旧利益,也是资本新势力,新利益。此次规定的出台也是站在城市整体出行管理的高度,推进出租车改革,整治专车的乱象,制约少数人对专车的过度消费。如果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可能随时有问题被击中,社会化成本很高。两者之间并非你死我活,而是充分利用新业态的增量带动老业态的改革。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司长刘小明在各方专家发言之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两位著名教授张维迎和周其仁分别总结发言。
张维迎教授在发言中主要围绕改革与市场的关系阐述了五点。第一,互联网专车是创新,是好事。但这个《暂行办法》如果真要实施,这个好事就做不成了,这是一个基本判断。当然,问题不在于主管部门故意,更多可能是错误认知,知识的限制。第二,不要与消费者为敌,这是任何政策基本的出发点和宗旨。消费者的选择是最重要的,就是要给他们自由的选择权。中国政府的传统总是要做保姆型政府,或者父爱型政府,老觉得老百姓都是小孩子,什么都不懂,容易受伤、上当。希望政府部门不要再把消费者当做不懂事的孩子,更不要与他们为敌。第三,要尊重商业自由和生产者权益。在市场当中每个人都有为另外一个人提供服务的权利,这与消费者主权是一致的。当汽车出现的时候,如果政府按照马车夫的利益来约束汽车行业的发展,也就不会有汽车。第四,监督经营者靠得是市场竞争导致的声誉机制。政府现在的管制规则都是建立在一个对市场误解的基础上,这个误解就是市场究竟靠什么维持秩序?我们没有弄清楚。其实市场就是靠声誉机制来维持秩序。第五,文件规定里有自相矛盾之处。限制了网约车,出租车的经营权就不可能真正取消,只是租金谁拿的问题。自由的、不受约束的网租市场,这可能是消灭出租车经营费的前提。

张维迎教授周其仁教授从自身做黑车的体验入手,结合他对中国城市化多年的调研,尤其是结合他对中国改革的多年心得,首先指出,法是黑白分界线,交通部不要轻易立个法弄黑一批人。中国生孩子有黑户,盖房子有小产权,开车有黑车。累积下来的“黑”已经不少,不要再添一批黑专车、黑拼车。治理网约车,必须着眼于大局,大局就是如何让消费者更满意,使城市运行也更高效。出租车不是一个独立的行业,而是大公共交通的一部分,而与公共交通抢占资源的是私家车。网约车不仅是技术驱动的新行业,还能提高私家车的利用率,甚至抑制私家车的购买,最终缓解道路资源的紧张,与公共交通一起更好的服务消费者出行和政府的城市管理,两者是互为补充,不是竞争,更不是你死我活,这是立法最应该着眼的点。最后一点是改革的思路要清晰,要大气。中央政府出台一个政策,试错的成本极高,应该充分利用中国的大国优势,利用不同城市间的差异,中央部委前期出一个指导性的文件,提出以人为主,鼓励创新,趋利避害,有序管理等纲领性的意见,让一部分城市先试先探索,中央部委后期再来总结。把各地成熟的做法由中央确认,全国推广,这是中国改革的宝贵经验。

周其仁教授研讨会最后还有激烈的争辩与问答环节,几位嘉宾之间争得面红耳赤。原来9点结束的研讨会一直开到10:30依然意犹未尽。
国家发展研究院官方微信
Copyright© 1994-2012 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65075号-1
保留所有权利,不经允许请勿挪用


